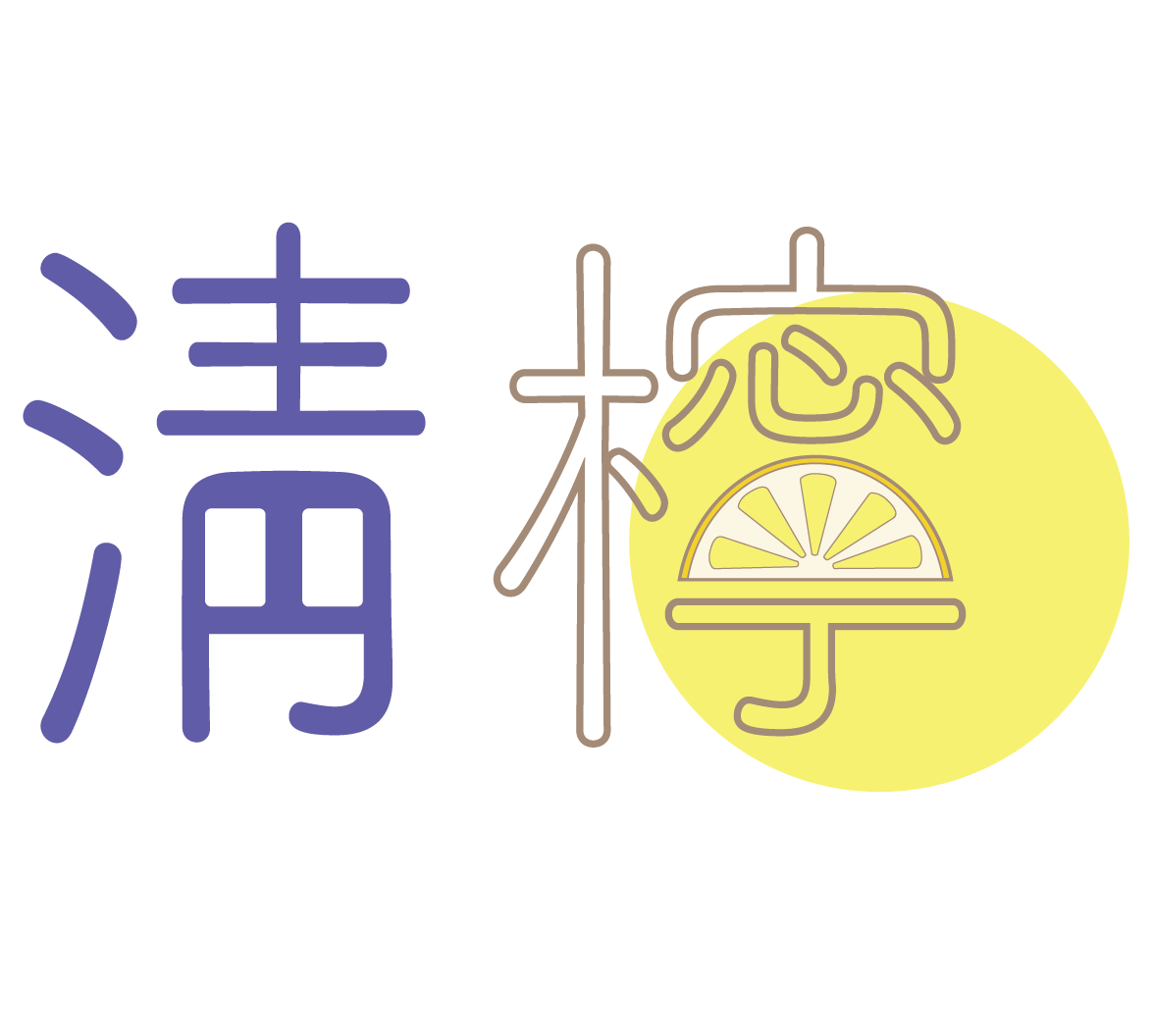磁帶、檔案與他們的時代:《磁帶:清華電台(1994-2018)》檔案電影嘗試

約莫在2021年左右,我在清大數位媒體創作社的社辦(時位於舊水木綜合社辦,即水木全家對面)尋獲了一批錄影帶,這批數量驚人的錄影帶覆滿灰塵,藏身在各種奇形怪裝的紙箱之中,只是,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些錄影帶裡面,紀錄了二十年前一群我們未曾謀面的學長姐們以及他們的時代。
▎保存與苦旅
我們理解影片與其他任何一項文化資產一樣,都是人類文化的載體,記載著珍貴的文化訊息,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去保護影片,一如保護任何一項文化資產,並要教育社會做如是觀……那是我們的責任去了解每一種載體的特性以及所代表的時代意義,以便更好的去處理人類活動影像的長久保存與影像遷徙(migration)問題。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所〈檔案人守則〉
清大數媒社的前身可以追溯回1994年成立的清華電台,當時他們以水木中心為據點,在校內發展以電台廣播為主的文化活動,並在後期逐漸引入影像等多元媒材的傳播與創作。一直到2010年代後期,因應大眾收聽習慣等轉變,成員逐漸減少的他們,最後併入了以影像創作為主的數媒社。也因此,大量他們曾經錄音及拍攝的素材也成為數媒社社團財產的一部分。
在面對這些學生拍攝的民間影像時,我們首當其衝的困境是:我們根本無從得知這些錄影帶中到底保存了什麼。這種「不可見的內容性」源自於兩個層面:一是磁帶載體與現代播放設備之間的技術斷裂(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二是轉檔所需的勞動與資金成本遠高於社團所能負擔。一段影像是否能成為「檔案」,並非來自它本身的歷史性,而是來自觀看脈絡與被重新介入的過程……然而在這之前,我們甚至無法「觀看」。
出於一種對影像與史料留存的直覺,我們主動向校友會、圖書館等校史單位尋求協助,希望能喚起對這批散落各處、未經整理的錄影帶的關注。這些錄影帶(多為 VHS 格式)本身即處在一種即將消失的技術邊緣。作為磁帶媒介,VHS 透過磁粉排列的強弱來記錄訊號,平均壽命約為 20 至 30 年,之後將面臨磁性衰退、訊號流失,最終完全無法讀取的命運。根據 2019 年國際影音檔案協會(IASA)的研究,多數 1970 至 1980 年代生產的磁帶,預計將在 2025 年前後達到不可讀的臨界點,應儘速將其數位化保存,這也被稱之為錄影帶的「2025大限」。
然而,我們的呼籲與焦慮如石沉大海般未能激起任何制度層面的迴響。面對這些技術性高但又脆弱的錄影帶,各單位往往缺乏認知與資源,也未將其視為檔案保存的一環。這暴露出個別單位的冷漠,以及一整套記憶制度的斷點——誰的影像值得保存?誰的歷史可以進入校史?
2023年5月,本校的蕭菊貞教授邀請了南藝大音像所的曾吉賢教授蒞校演講,主題好巧不巧,就是音像所長期致力於的影像保存與修復。隨著曾吉賢教授在台上漫談他們在全台各地展開的搶救工作、數位轉檔的技術瓶頸,以及影像作為文化遺產的脆弱與價值。但是,我在台下一邊聆聽,一邊盯著前排幾位校內長官的後腦勺時,卻感到一陣眩暈——我們的錄影帶正堆在辦公室的櫃子裡,一捲一捲的等待著死亡。我們看著「影像保存」成為講座中公共價值的某種宣言,為什麼這些講求歷史責任與文化倫理的論調,沒辦法在校內轉化成具體的資源與制度?
冒著冒犯的風險,我在演講後的 QA 時段向曾吉賢教授提出了這個問題。實際上,這句話是說給台下的一排長官聽的——包括時任藝文中心主任與圖書館館長在內。或許,這樣的頂撞是不得不為之的。面對一層層冗長的官僚系統與斷裂的溝通管道,這樣的場合,反而成了我們拯救這批影像檔案的最佳也是唯一的契機。
出乎意料地,在圖書館館長的當場承諾下,我們終於看到一些希望:部分錄影帶被移交至圖書館特藏組保管,他們也口頭保證將會進行修復與數位化保存,並在完成後通知我們。
但事實上,當初送往圖書館的檔案僅佔了不到一半,我們還存有一整箱的錄影帶及兩箱的錄音帶,內容為清華電台的節目錄音,這些已經超出特藏組願意處理的數量。

▎成為檔案的必要
檔案電影研究學者Jaimie Baron將所謂「檔案效果」(Archive Effect)定義為:一種觀眾在觀看影像時產生的感知反應,認為這段影像來自於不同於主要作品製作時間與語境的歷史時刻,因此賦予這段影像一種「檔案」的地位與真實性。
約莫一年多後,在策劃清大交大風夜電影節的過程中,我忽然想起那批檔案影像。或許是出於好奇,或是一種純粹的觀看的慾望,我動筆寫下了一份關於如何運用與活化這批影像的計畫書,並寄給了圖書館特藏組。
出乎意料地,特藏組回覆的態度竟相當正面——對於一路上屢屢受阻、飽受冷言冷語的我們而言,這沒有疑問的令人感到振奮。
在他們的安排下,我們得以進入圖書館,觀看那批已完成數位化處理的影像:儘管特藏組因為經費限制,只完成了一半數量的轉檔,但是看到總時長超過150小時左右的錄影帶影像被保留下來,著實令人激動。
我想,正如許多檔案一樣,這些影像令人興奮的點不僅僅在於它被記錄下的時空環境,還有它本身的生糙及未經處理:無意識的長時間凝視、仰賴機內剪輯(或許不存在)的觀點、緩慢而不確定的對焦跟變焦。
它的另一大特點來自於它的「冗長」——或是說它巨大的體量及缺乏編碼的狀態,我們必須仰賴殘缺的影帶側邊標籤,以及時有時無的影像內資訊來判斷這部影像拍攝的年代及地點;它的拍攝涵蓋了2000年前後校園內的各種事件,包含社團活動、演唱會、大量的梅竹賽影像、學生會議、校方公聽會、戲劇片段或是各式各樣的生活碎片,同時,隨著部分影像已經遭受一定程度的毀損跟失真,留下的僅是模糊不清的背景音與扭曲變色的景象。而正是在這樣的影像特質中,我們感受到檔案與歷史之間的無意識關係:這些影像非為歷史而拍攝,卻因其留存與再現的機會,而被納入歷史敘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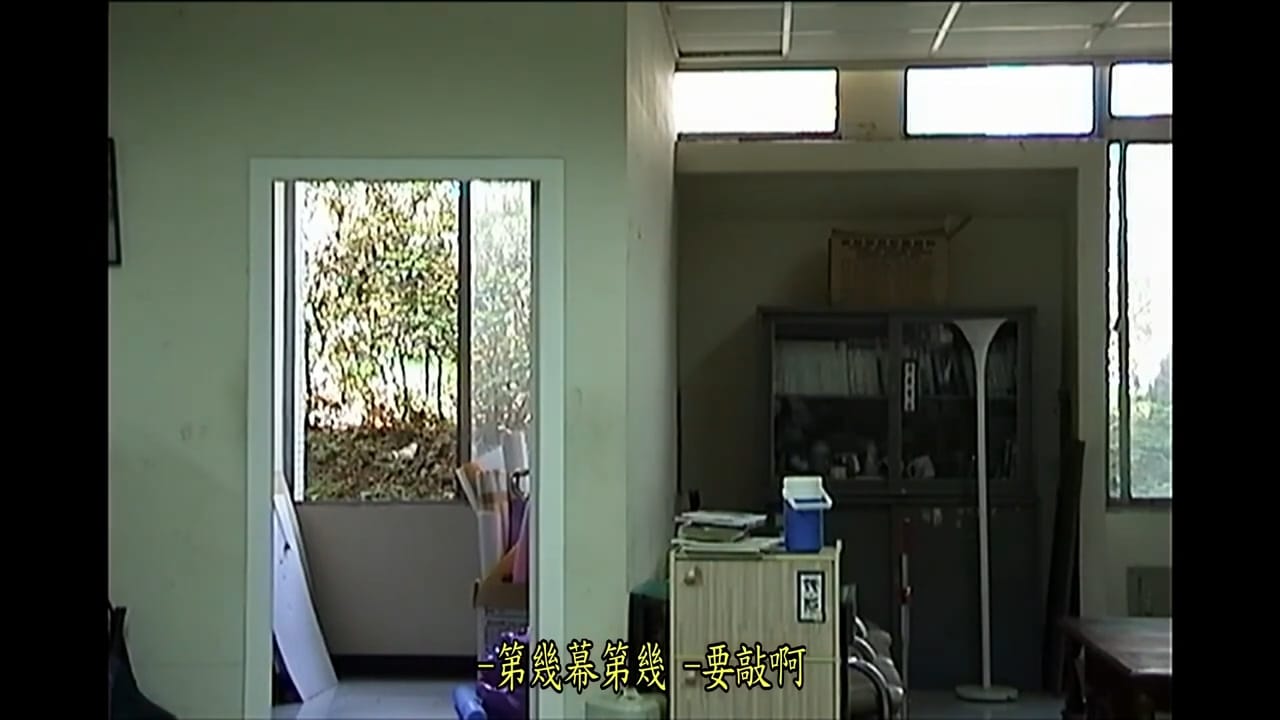
這就是檔案紀錄片與其他紀錄片最大的差距:這些素材完全不屬於敘事的意圖,它們有時甚至與任何清晰的訊息或用途毫無瓜葛;這些影像存在的目的便是自身,而不產生結果,僅僅是過程而已。也因為如此,觀者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訊息的主體,而是被迫成為積極的閱讀者:我們必須反覆觀看、停格、猜測、補足空白,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種「詮釋的權力」開始從拍攝者轉移到我們作為剪接者的手上。
但這種權力不是無害,它也隱藏著風險與倫理困境。這些陌生的面孔,這些我們不知道名字、無法確認生死的人們,在我們今天重新觀看的行為中,被納入另一個敘事。我們建立一個他們未曾參與建構的記憶框架,他們的出現既真實又幽靈般不確定,他們像是檔案中的鬼魂(specters of the archive),喚起我們遺落之物的責任,也讓我們警覺「觀看」這件事從來不是中立的。

▎磁場與數位的考古
為了完成這部影片,我在圖書館特藏組瀏覽完所有轉檔完成的影片之後,挑選了總時長約為80多小時的素材,複製、備份、返回我的電腦前,展開了漫長的剪輯工作。有趣的是,許多意圖「失準」的影像,卻意外成了我們與攝影機前面與後面的鬼魂們的溝通線索:在他們精心打造的一段敘事架構——可能是棒球賽轉播、一段意義未明的劇情短片或是活動排練的紀錄——之外,洩漏出了更加真實、更加原始的模樣,那是過早或是過晚開錄的影片、賽前試圖熟悉機器操作的片段,以及在同一捲錄影帶上重複錄製時,可以看到機內剪輯下留下的雜訊痕跡。
我將這樣的真實反覆揀選出來,試圖在時間軸上排演出一場有意義的生活,使我們足以想像,當初是誰如何扛著這台攝影機,在校園的哪一個角落,意外的使捲動的錄影帶將光影投射到二十年後來。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觀看他人生活的種種原因裡,哪怕是一個頑固而零碎的欲望,都在投射裡面找到一個什麼東西得以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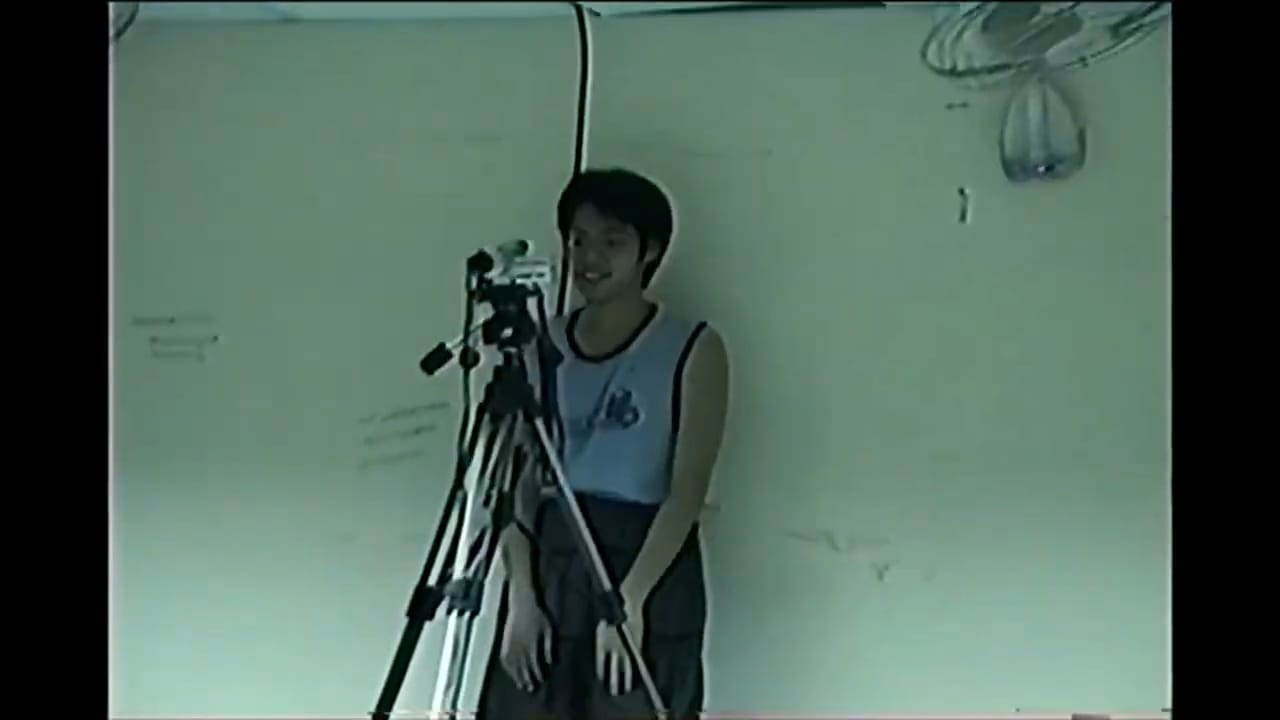
重新回頭看去,我竟慶幸自己剪輯時留下了許多電台辦公室及錄音室內部的片段,在本片完成不久,電台舊址、同時也是(我與一眾社友共同度過數年大學青春的)數媒社辦公室的共同社辦,就被學校收回並重新裝潢。儘管我們只能猜測,但在影像裡耗費青春與音樂、影像和友誼打交道的大學生們,或許與我們共享相同的鄉愁;這些片段因此成為我們鄉愁的部分,不僅保存了那些無名的面孔與偶然的事件,也保存了我們自己——保存了那個在錄影帶上看見過去、在過去中看見自己的時刻。
檔案影像並不會因為缺乏完整的敘事而減損價值,反而因為它們的殘缺,才能在不同時空下開啟對話。二十年前有人按下錄影,二十年後我們重新播放,而時間即得以在其中折疊。

在形式上除了素材揀選的策略之外,我也思考素材本身的處理手法。與膠捲不同的是,雖然錄影帶維持了長條帶狀的物理結構,但它帶給人們在影像上觀看的自由度卻遠勝於膠捲,錄影帶的發明,使得人們擺脫了電影一秒24格的速度限制,不在依賴放映師與放映機的幫助,而是透過遙控器和錄影帶放影機,所有觀者都可以自由的選擇播放速度和觀看的時間點。在處理這部影片時,我嘗試將這種媒材特性在梅竹賽素材的混剪中凸顯出來,透過大量影像的多時點堆疊、不同的變速處理、乃至於「倒帶」(這一詞也來自錄影帶文化)的蒙太奇,將錄影帶特性植入了數位化後的影像之中。好像如此,我們也得以完成某種對於這項消逝媒介的致敬。
鄉愁的召喚也好,對錄影帶的致敬亦同,我們無非是在進行一場微小的、個人的影像考古,翻動時間空間的感官召喚,還接近媒介考古學所揭示的,去觸摸一種已被技術革新淘汰、卻在物質形態與觀看方式上依然存活的時代經驗。
錄影帶的快轉、倒帶、暫停、反覆觀看,本身就是類比年代的觀看邏輯。
▎結語
《磁帶:清華電台(1994-2018)》在2024年的風夜電影節完成了放映,其中還搭配了共同策展人張念晴為本片創作的精彩配樂,希冀能更臻完整,然我未能在片中完全解決及呈現以上提出的一些問題與想法,而僅僅只是觸及的層面,而這部分,希望留給觀眾去行批判。
然而,真正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很多東西的不為所動。
數媒社長期保存電台所遺留下來的,除了大量錄音帶、錄影帶之外,還有許多見證類比時期聲音生產的廣播設備,這些原本可做為校園歷史與文化記憶的重要媒介資產,卻在2024年,因課外組要求縮減儲藏空間以配合校方規劃,不得不進行處置。當時課外組口頭承諾會「聯絡特藏組並妥善處理」,但最終卻將這些設備逕行報廢,令人失望。
2025年初,學校再度決定收回課外組水木中心一樓空間,亦即過去清華電台的舊台址與數媒社辦公室,作為招商使用。面對接連而來的空間與制度變動,我們不得不開始思索,該如何處理社團仍然保存的大量錄影帶與錄音帶資料。最終,考量特藏組有限的典藏與修復能力,加上校方或許仍然匱乏的文化資產保存意識,數媒社決定將這些遺留的影音檔案全數捐贈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保存中心,盼能在更專業的環境中獲得延續。

要是我們未能阻止那些設備與磁帶被送入報廢場,就如同我們未能在影像中說出所有故事。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影像尚未終結。它們會在不同的地方被重新發現,在每一次播放中的凝視與凝視之間,延續記憶和無人聞問的過往……它們被留下,不是為了成就某種大敘事,而僅僅只是存在過。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思索:記憶的機制該如何承接這些「無法成為歷史」的素材?當我們對這些檔案的態度是遺忘而非對話,我們是否還有可能創造其他形式的公共記憶空間,使那些曾被遺棄的聲音,重新獲得發聲的可能。
記者/夏兆辰
編輯/魏欣平
照片/林以嵐 、夏兆辰、《磁帶:清華電台(1994-2018)》
#檔案電影 #影像修復 #校史